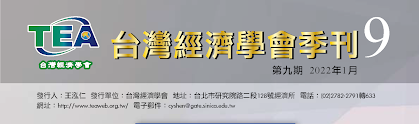轉載自 台灣經濟學會季刊 -- 第9期
PDF檔
底下是網頁易讀版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0月11日揭曉, 由三位美國經濟學家: 卡德 (David Card)、安格里斯特 (Joshua Angrist) 以及因本斯 (Guido Imbens) 共同獲得。這三位經濟學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 透過對於資料的統計分 析, 評估公共政策的效果, 其中, 尤以卡德在最低工資與就業率關係的議題中, 奠定實證研究在政策效果評估的重要地位。
卡德與其合作者克魯格 (Alan Krueger) 透過檢視提高最低工資的紐澤西州資料, 並以鄰近未調整最低工資的賓州作為對照組, 發現最低工資調漲後,反而使得速食業的聘用人數增加。傳統經濟學的觀點是, 提高最低基本工資將導致低技術勞工失去工作, 而卡德與克魯格的研究結果挑戰了這個傳統智慧。卡德與克魯格的論文對於經濟學研究與公共政策帶來了若干啟發。首先,經濟學理論或是傳統智慧必須經得起資料與統計分析的驗證,尤其是當這些經濟理論攸關公共政策如最低基本工資, 消費券發放等。其次, 無論是公共政策的辯論與決策, 都需要基於實證證據。當然,這兩個觀點也同樣適用於貨幣政策的討論與執行。
在有關貨幣政策的討論中, 我們也時常看到一些對於台灣央行政策解讀上的歧見。舉例來說,央行宣稱自己執行的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近年來稱為彈性匯率政策),新台幣匯率原則上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 唯有遇到匯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動,而有不利於經濟與金融穩定之虞時才會干預。然而, 部分媒體與市場人士透過觀察央行的外匯市場干預行為, 卻認為央行傾向於執行「阻升不阻貶」的匯率政策。在新聞資料庫中搜尋 「阻升不阻貶」這個名詞, 最早可以追朔到中央日報 2001 年記者胡秀珠的報導, 標題為「日圓巨貶, 台股匯市雙重挫,大盤跌126點, 台幣跌1.27角, 央行阻升不阻貶, 成交爆大量, 增逾10億美元, 34.707作收」, 而經濟日報 2002 年 7 月 27 日記者應翠梅的專題報導, 亦直接下標「央行阻升不阻貶」。值得注意的是,當媒體或是市場人士批評「央行阻升不阻貶」 時, 相信並非以字面上的意義: 「央行在外匯市場上只阻止升值, 並不阻止貶值」 予以詮釋。相反地, 應該是 「 央行不願台幣升值, 願意台幣貶值, 故平均而言, 央行在新台幣升值時採逆風干預的次數較多, 在新台幣貶值時, 採放任不管的次數較多。」 因此, 以平均概念來思考所謂的 「阻升不阻貶」 應該較為適當, 畢竟央行不可能也不該 「在外匯市場上只阻止升值, 卻不阻止貶值」。 因此, 當觀察到央行偶有阻止新台幣貶值之跡象, 少數媒體就會出現 「央行以具體數據破除匯率政策阻升不阻貶」 的說法, 顯然是錯誤詮釋 「阻升不阻貶」 的本意。 當然, 無可否認的是, 「阻升不阻貶」 是一個較為口語的敘述, 嚴謹的說法應該是 「非對稱干預」(asymmetric intervention) 或是 「單邊干預」 (one-sided intervention)。
關於央行是否執行 「阻升不阻貶」 的匯率政策, 官方的回應從未更改, 一概否認到底。 早期只是不斷重複一些空洞而無益於政策討論的說詞。所幸, 在 2014 年 12 月 18 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參考資料的回應中, 我們看到央行試圖根據資料做出較有意義的政策討論。透過觀察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資料, 央行宣稱: 「新台幣對美元價位有升有貶, 且長期間呈升值的趨勢。」 如果進一步以有效匯率指數來看, 則是認為 「新台幣對一籃通貨的匯率走勢亦呈現有升有降, 三年多來則呈走升。」央行願意就實際資料進行討論, 確實是一大進步, 但是匯率動態本來就是反映各種不同衝擊, 只透過觀察到匯率長期間呈升值的趨勢, 是不足以當成央行沒有 「阻升不阻貶」之證據, 這就如同學生不能把 「考試成績不及格」 當成 「沒有作弊」 的證據一樣。 此外, 資料也需要透過嚴謹的統計分析進行推論, 像這種以眼球計量經濟學 (eyeball econometrics) 所得到的結論, 並無法令人信服。學界對於「阻升不阻貶」的早期研究也是專注在匯率動態。舉例來說, Shen and Chen (2004) 是早期探討央行不對稱干預政策之研究。他們透過馬可夫轉換模型發現新台幣匯率在升值時會有「長幅擺盪」(long swing) 現象, 在貶值時則會有「短期擺盪」 (short swing) 現象。他們將這樣的實證結果解讀成央行在升值時採取阻升政策(slowdown policy); 貶值時則消極面對, 採不阻貶政策 (let-it-go policy)。 然而, 雖然透過計量方法的檢視, 可以避免所謂的 eyeball econometrics, 但是只觀察受到政策影響的目標變數, 如上所述, 依然無法提供「阻升不阻貶」的直接證據。
對於如何刻劃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行為, 學術界做出不少努力。 一種做法是透過估計央行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進一步探討央行的貨幣政策是否因面對新台幣升貶而有不同的反應。沈中華與徐千婷 (2000) 利用馬可夫轉換模型估計一個貨幣基數政策法則,結果發現在這段樣本期間中, 央行在面對新台幣大幅升值時, 提高了貨幣基數反應函數中匯率目標的權重。而陳旭昇與吳聰敏 (2010) 則透過估計一個利率法則的門檻模型發現, 央行於 1998 年後, 在新台幣升值時, 干預外匯市場, 採寬鬆貨幣政策; 新台幣貶值時, 央行不阻貶, 甚或可能推波助瀾地助貶。姚睿, 朱俊虹, 與吳俊毅 (2010) 採用即時資料 (real time data) 亦發現, 當新臺幣貶值時, 央行可能進一步採寬鬆的貨幣政策讓貶值幅度擴大。相反的, 吳致寧等 (2012) 在考慮所謂的偏誤修正變數 (bias correction terms) 於門檻模型後發現, 央行不論在新台幣升值或貶值時, 均採取阻升又阻貶的逆風干預政策。 林依伶, 張志揚, 與陳佩玗 (2012) 則延續上述研究, 考慮新台幣大幅升值, 大幅貶值以及小幅升貶值三種不同的區間, 亦發現央行在新台幣大幅升值或貶值期間皆採逆勢干預的貨幣政策。最後,吳若瑋與吳致寧 (2013) 進一步透過與吳致寧等 (2012) 相同的門檻模型, 配合即時資料的使用, 結果發現央行之貨幣政策具 「阻升助貶」 之特性。
然而, 估計央行的利率政策法則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 利率的變動只反映了間接干預。由於台灣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直接買賣外匯才是其最重要且影響力最大的干預方式, 因此, 想要了解央行的干預政策, 就應該透過檢視匯率以及央行外匯買賣行為之間的互動。然而,研究者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 央行並未公布外匯買賣干預的歷史資料。一般而言, 在缺乏實際干預資料下,都以外匯存底或是央行國外資產的變動量當作央行匯率干預的替代變數。利用外匯存底或央行國外資產變動作為替代變數有兩個潛在問題: (1) 未排除外匯資產孳息, 以及 (2) 未考慮外匯存底中不同外幣資產價值變動。第一項無須多做解釋,第二項問題則是因為外匯存底中包含其他外幣資產, 假設歐元相對於美元貶值, 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存底價值就會縮水。
為了剔除匯率變動因素, 陳旭昇 (2016) 遵循王泓仁 (2005) 的做法, 使用 「準備貨幣增減因素 - 國外資產」作為央行匯率干預的替代變數。實證結果發現,無論匯率干預政策是為了因應實質匯率衝擊或是名目匯率衝擊, 央行在 1998 年 3 月前後的匯率干預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在1989 年 5 月 到 1998 年 2 月之間, 央行對於外匯市場的干預較小。反之, 證據顯示在 1998 年 3 月之後, 央行對於匯率確有顯著的 「阻升不阻貶」 之行為。
在無法取得實際干預資料的情況下, 資料的侷限性促成另外一支文獻的發展: 透過媒體資料探討央行的匯率政策。 張興華 (2013) 以及柯秀欣 (2016) 以媒體報導之央行外匯干預新聞作為央行干預的代理變數, 結果依然發現, 相對於阻貶而言, 央行的匯率政策有偏好阻升的現象。 總而言之, 文獻上對於央行是否採行 「阻升不阻貶」 的匯率政策雖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除了少數有央行研究人員參與之論文發現匯率政策與央行的官方說法較為一致 (參見吳致寧等 (2012) 以及林依伶, 張志揚, 與陳佩玗 (2012)), 其他論文大多發現央行確有「阻升不阻貶」甚或是 「阻升助貶」的「害怕升值」 行為。 事實上,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根據一篇刊登在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的最新研究: "QE 的 15 道陰影" (Fifty shades of QE: Comparing findings of central bankers and academics, Fabo et al., 2021), 作者比較 54 篇論文發現, 與一般的學界研究相比,有央行研究人員參與的論文較容易發現量化寬鬆(QE) 政策有效, 且其效果較大亦較為顯著。 此外, 作者也發現, 能夠證明QE 政策對產出有較大效果的央行員工, 相對於其同儕比較容易獲得升遷。
為了解決無法取得實際歷史干預資料的問題, 早期文獻如 Weymark (1997) 試圖以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的理性預期貨幣模型建立外匯市場干預指標 (Weymark Index), 但是該指標已被 Chen and Taketa (2007) 證明並非一個好的央行干預替代變數。在最新的研究中,Adler et al. (2021) 對外匯存底變動做孳息與資產價值之調整, 並建立一個包含台灣等 122 個國家的匯率干預指標替代變數。而李秀雲 (2021) 則是將台灣外匯存底的變動分解成干預、外匯孳息與資產價值重估三部份。根據其實證結果發現, 在 1982-2015 年間, 外匯存底增加近六成來自孳息、四成多來自淨買匯干預。
然而, 除了考慮外匯孳息與資產價值重估之外, 台灣的央行外匯干預估計還有其他問題。由於台灣央行透過現有的會計制度, 巧妙地讓部分外匯資產不放在外匯存底的科目下, 而是「藏」 到其他不起眼的科目中。 央行在 2020 年 3月之前, 並沒有根據 IRFCL 明確揭露相關的外匯衍生性金融交易以及外匯資產借貸。 因此, 透過「換匯交易之外幣部位」、「存放國內銀行業之外幣」 以及 「對本國銀行外幣拆款」 這些科目「隱藏」 約1400億美元的外匯資產, 這反應過去以來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規模, 遠遠大於外界的認知 (參見吳聰敏, 李怡庭, 與陳旭昇, 2020)。
因此, 唯有央行能夠公布外匯干預的歷史資料, 我們才有機會客觀評估央行的外匯政策。根據 Adler et al. (2021) 最新的整理與研究, 近年來, 全世界已有 43 個國家 (包含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的央行, 大多數已經公布距今約1年之前 (2020年9月之前) 的央行買賣外匯的外匯市場干預歷史資料。 其中, 36 個國家公布月資料, 7 個國家公布季資料。 公布歷史資料, 對於當前外匯市場的交易與運作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在這些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之中, 從未聽過哪一個國家因為公布歷史資料造成經濟與金融運作上的重大傷害。
依據行政院第 3322 次院會決議指示, 政府開放資料 (Open Data) 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滿足產業界需求, 對於各級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而中央銀行資料開放行動方案(2019年12月修訂) 亦提到, 央行資料開放的預期成效為:
"增加政府施政透明, 透過民間無限創意及自由加值運用, 以活化政府資料應用。"
或許一般人對於央行干預外匯市場資料沒有興趣, 但是一般人對於央行的匯率政策施行是否適切, 決策是否符合預期目標當然會有興趣, 畢竟央行的貨幣政策決策與我們的經濟生活息息相關。 因此, 不該以 「僅有少數人有興趣」 為理由, 拒絕公布外匯干預歷史資料。
舉例來說, 央行在理事會舉行一個月後會公布議事錄摘要, 而台灣多數人對議事錄摘要不感興趣, 也不會特別去閱讀。 既然議事錄摘要只是少數人有興趣的資料, 議事錄摘要又有何公布的必要? 事實上, 透過議事錄摘要的公開, 得以讓少數對議事錄摘要有興趣的人 (如媒體記者與學者), 對議事錄摘要做重點報導或是解說, 使得大眾對於央行決策有更深刻的體會與了解。 同理, 央行公開外匯買賣的歷史資料, 讓少數對歷史資料有興趣的人, 透過嚴謹的分析與說明, 使得一般大眾更加能夠了解央行政策執行的良莠。 歷史資料的公開, 當然是民主社會中, 貨幣政策透明化與可究責性的重要一環。 經濟學家可以透過資料分析, 說明 3 倍券的政策效果, 當然也應該要能夠取得歷史資料, 分析與檢討過去貨幣與匯率政策的效果。
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開放, 路途中最可貴的進步就是, 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神聖而不可質疑。 然而, 為了讓政策的討論與檢視不會流於沒有根據的各說各話, 政策討論的起點就是讓實證證據說話, 而開放歷史資料正是理性政策辯論的起點。